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余向荣
中国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存在较大温差。上半年对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出口和非住房类投资,但其对居民收入和资产价格传导不畅,消费活动尚缺乏动能。出口有周期性,也遇到越来越多地缘政治阻力;投资面临债务上升、回报率下降等挑战,而且进一步强化供应,会加剧未来的供需不平衡。这种“双轨式”复苏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性叙事帮助不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直接着力提振消费、畅通内循环既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需要,也是扭转公众和市场预期的关键。
消费再平衡不是新话题,只是到了需要更加重视的时候。从伯南克2005年针对中国提出“储蓄过剩论”算起,讨论再平衡有20年了。到目前为止,进展依然非常有限。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过去20年均未超过40%。疫后消费取得了恢复性增长,但去年消费率也就39%,社会零售总额跟疫情前趋势比反而拉大了差距。随着经济增速趋缓,一些因素使得我们现在政策重心需要向消费倾斜一些:
第一,经济体量。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,市场占比约15%;去年出口3.4万亿美元,差不多等于印度GDP(3.7万亿美元)。有的行业,中国产能已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绝对优势。在传统行业,像粗钢产量,中国占全球55%;在新兴行业,中国光伏产能全球占比近90%,锂电池产能约80%,电动车产量占全球销量65%。
第二,地缘政治。经历中美贸易战、疫情冲击,各国都更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,更注重本国工业发展。先是美国对中国战略产业大幅提高关税,再是欧洲对中国电动车和绿色产业进行反补贴调查,未来不排除在全球南方也会出现反弹。
第三,民众获得感。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居民福利,消费是获得感的体现。去年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约2%,今年上半年再降超5%。与其补贴海外消费者或降价对冲关税,不如提升国民福祉。
如何提振消费?我想这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消费,避免“节俭悖论”。消费也是一种投资,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,而投资是延迟的消费——不能无限期延迟。要推动消费再平衡,可能也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“涓滴经济学”的政策思路:从出口和投资再传导到消费,不如直接刺激消费。具体地,我这里提几点粗浅的建议:
第一.切实推进发展这个“第一要务”。面临外部不确定性,防风险固然重要,但“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”,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——包括消费。经济发展了,消费才有活水之源。
第二.让居民收入增长高于名义GDP增速。消费是收入的函数。支出端要扩大消费,收入端就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分配比例,尤其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。我建议我国借鉴日本1960年代池田内阁经验制定一个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,将收入增长更明确地纳入政策评价体系,动员各方面力量提振居民收入。政策上可以引入雇员工资动态调整机制,让薪资增长至少可以追平通胀。同时,要重振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信心,毕竟他们创造了80%的就业。让民企在市场准入、要素使用、政策支持等方面享有公平待遇、避免选择性执法是第一步。市场化、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可预期、稳定以及取向一致的政策环境则更加重要。加强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亦应是重要一环。
第三.筑牢社会安全网。居民收入分配占比扩大的空间必然是有限的,因为它会挤压企业和政府的份额。工资增长会侵蚀企业竞争力,而制造业仍是我国战略支柱。很多政府支出也有刚性。但消费再平衡还可以通过降低储蓄率实现。我测算去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为36%(美国约4.5%),有巨大下调空间,而其前提是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。比如,要发展银发经济,那就要做实养老金账户。今年养老金还能涨,未来十年随着“婴儿潮”一代退休,养老压力会进一步加大,我们需要提前做出应对安排。我们也应建立起与消费社会相适应的住房体系。通过政府回购等形式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可以减少“住房储蓄”,但除了央行再贷款,作为公共品提供,财政参与不可或缺。多管齐下稳定商品房市场也是避免负向财富效应、重振消费者信心的必要条件。如不扩大政府收入分配占比,那就需要其支出结构更多从基建投资和产业补贴转向民生。
第四.大力补贴生育。养育成本高企是生育率走低的主要原因。例如,我国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.5%,而发达国家普遍50%以上。中国80%以上婴幼儿由父母和祖父母照料,到第二、第三胎他们就不堪重负了。又如,我国人均居住面积42平方米,一二三线房价每平分别约4.4、1.3和0.97万元,增加一个家庭成员的居住成本约为184,56和41万元。所以,生育补贴一定要足够大才能扭转趋势,避免像韩国那样滑入“人口紧急状态”的风险。去年新生儿902万,如果一人一次性补贴36万元(相当于18岁前每年2万),一年3.2万亿元,相当于GDP的2.6%;相比之下,我国一年基建投资超17万亿元。即便在现有财政框架下,这也是有空间腾挪的。但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,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扩容募集增量资金用于长期人口战略投资,乘数效应会更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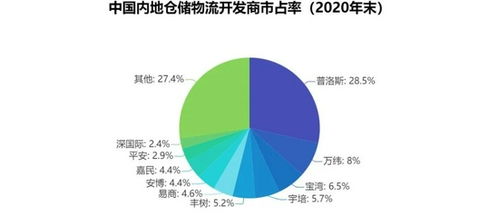
第五.唤醒土地价值。我曾做过测算,农村土地财富可达150万亿元,按户籍人均近20万元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.4倍,部分是因为前者有更多财产性收入。城市有成熟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,而农村土地和不动产很大程度上不可交易。允许农民土地使用权、特别是宅基地使用权在更广范围内流动、交易、抵押,可以有力地释放农村土地价值,也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化,使新市民在城市安居后可以负担生活和住房成本。除财富效应,市场化的土地权益也有助于农村居民获得消费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。
第六.突破消费场景限制。还是要确立一个市场化原则,减少对消费行为不必要的行政性干预。比如,商品房限购现在已经放宽,相信未来还会放得更宽。很多人认为,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已趋近发达国家水平,因此住房需求已基本饱和。如果按照现行居住模式,这个判断也许没问题;但纵观世界各国,不少人口密度大于中国的国家,大部分居民也是住在多层或独立屋。所以,打开思路,我们居住条件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。又比如,中央现在要求对汽车的限制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,也会释放出更多消费潜力。
最后,我这里说的是“再平衡”,不是说投资不重要。相反,我认为投资很重要。我到过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调研,其中一些地方就是选举前发钱消费,余向荣:是时候推进消费再平衡了选举后收缩财政,缺乏长期投资,经济陷入一个不断反复的“消费陷阱”,难以增长。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大量投资,现在既有条件也有必要向消费倾斜一下。